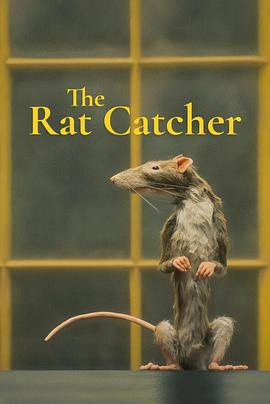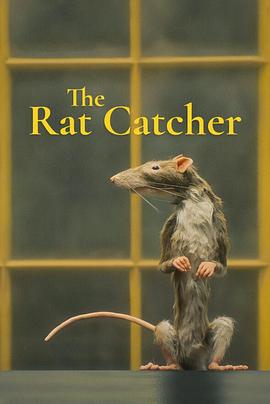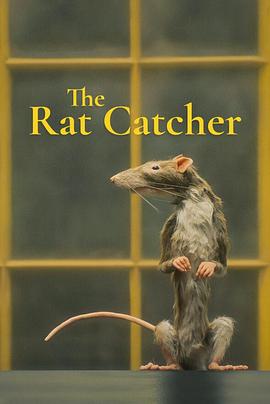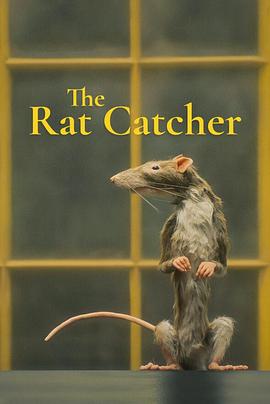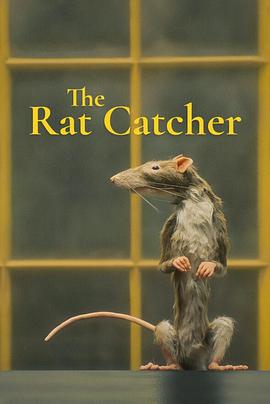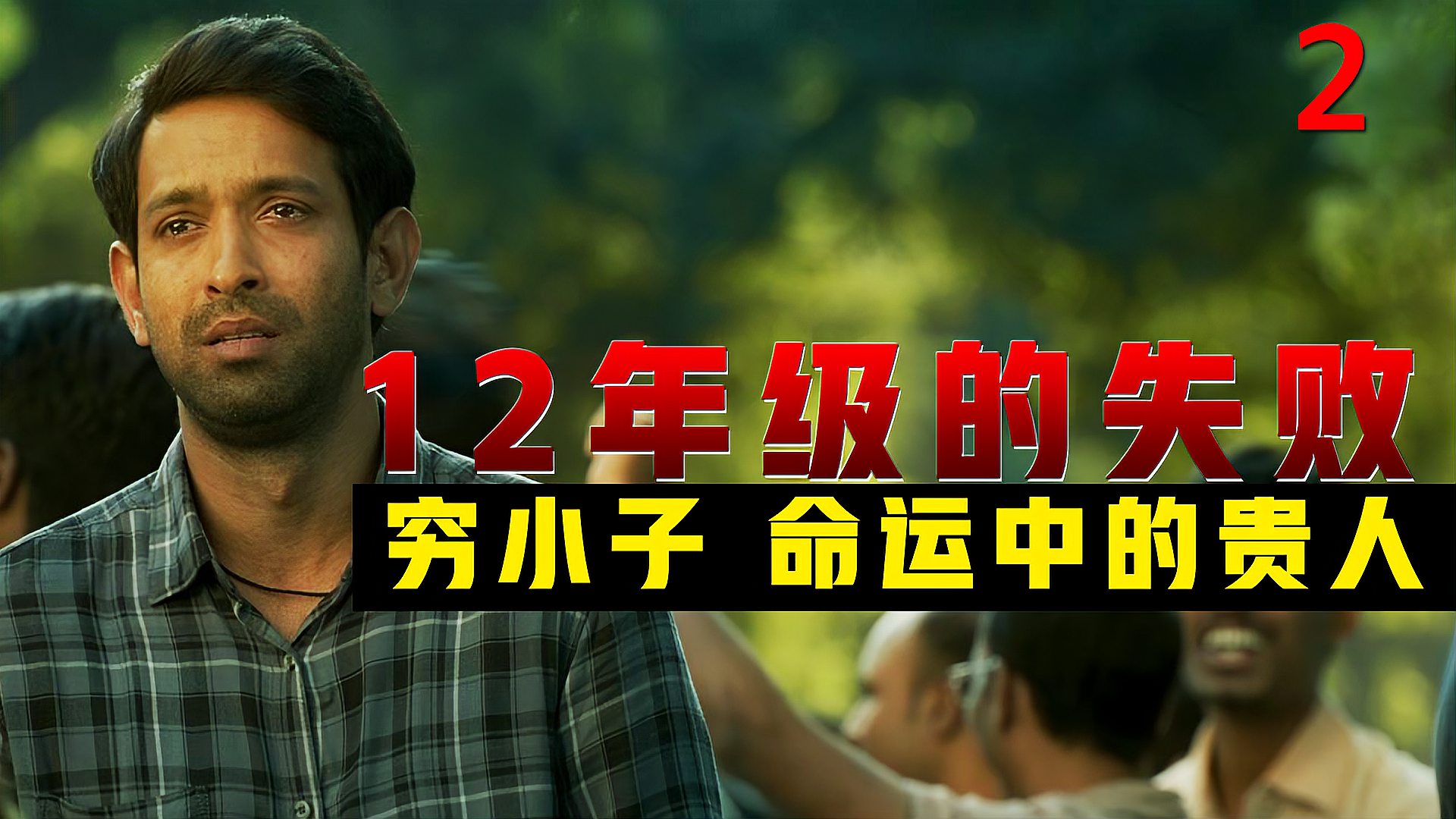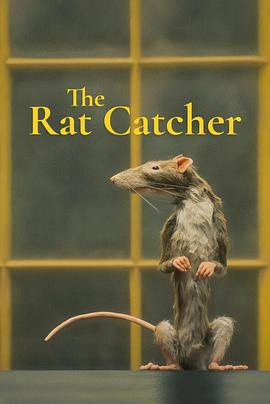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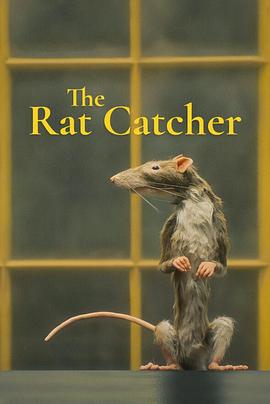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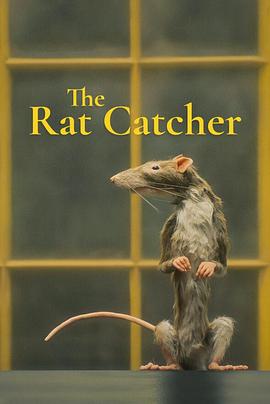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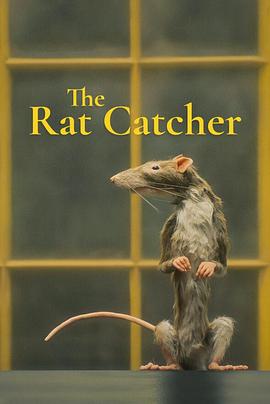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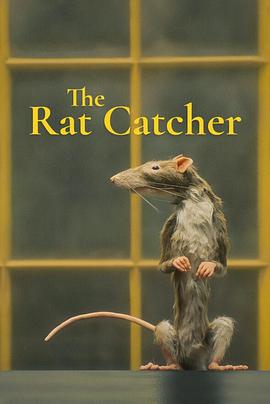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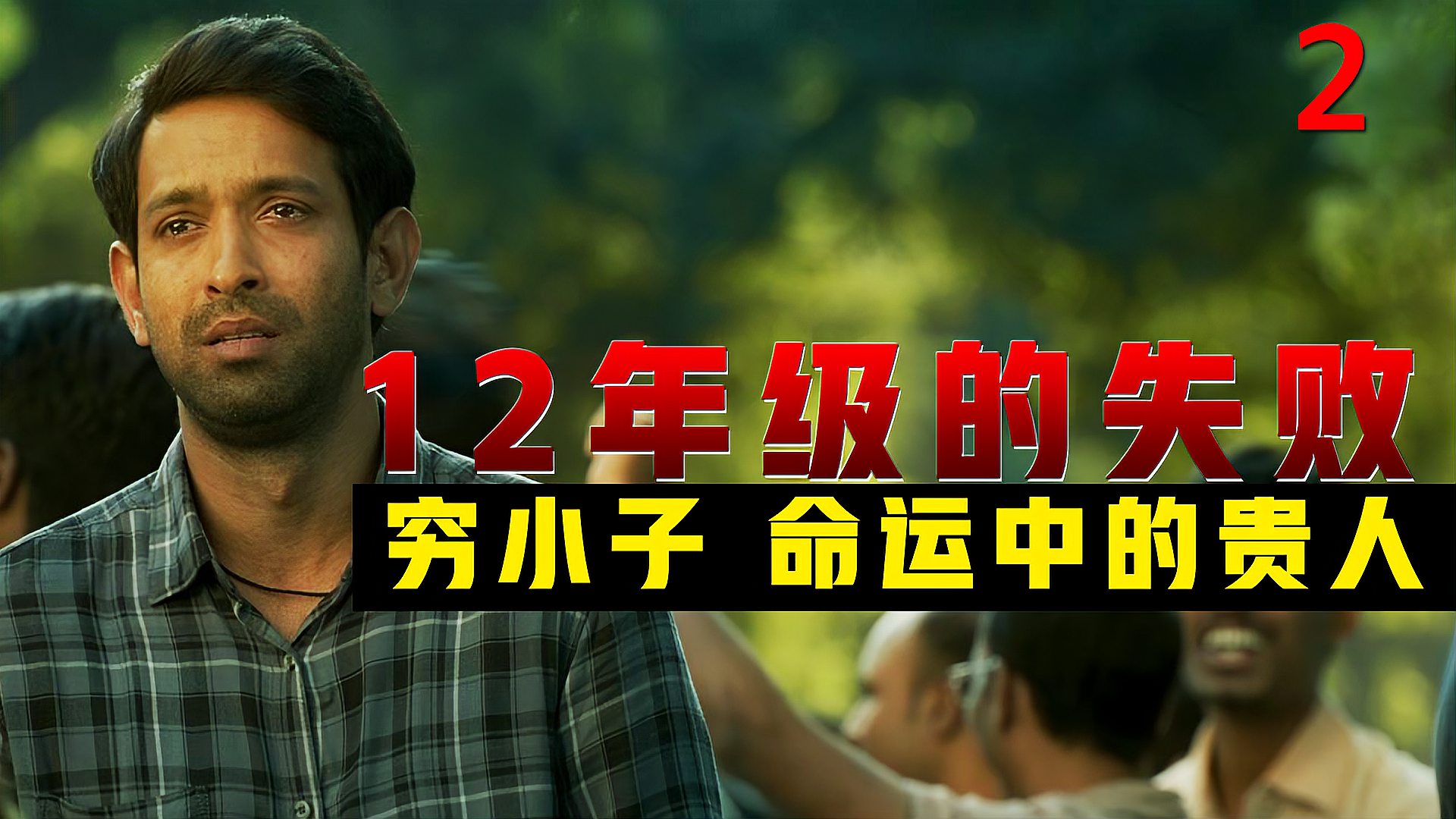




如果说上部停留在对疾病本身的探讨和阐释,下部便以宗教为注脚,上帝与爱人的类比成为疾病的一体两面(上帝抛弃天使和人类,爱人抛弃疾病和爱情,皆隐含末日意味),疾病的意义空间向“意义”本身扩张,宗教的先进(倡导死亡)与保守(提倡没有死亡的世界)并存,爱情的嗅觉(身体分子化)与味觉(皮肤液体化)并存。从爱情谈及宗教(或曰反之),天使成为传播中介,千禧年后的混沌成为“重建”世界秩序的契机,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对人类关系(个体/群体)的修复,当作为先知的凡人将私爱升华至博爱,选择尘世疾病和痛苦,选择成为“感受”的载体,选择成为“世界公民”,宗教学(或被戏谑地称为天使学)意义对人类来说还剩下多少——或许比“上帝已死”的论断更觉残冷,但是“疾病带走了我们很多人,但不是全部。世界只会向前发展,我们都将成为公民。”虽是架空,但对三国格局的借鉴,沿袭第五代对历史题材的偏好,即使经过“新千年”的几轮翻盘洗礼之后,依然能清楚触摸到“古老秩序中的一幕有唱有和的权力与情理的游戏”;也能窥见美学追求上的专注与提升,水墨画风浩渺氤氲,黑白灰色调的渐变层次极具光感质地;古音缭绕间权谋捭阖,人心博弈,螳螂捕蝉之术千年不衰。练剑峡谷与决斗现场的空间设置好,在空旷历史舞台上,个人的存亡无法撼动权力世界的秩序。镜像作用与偷窥视角、屏障与纱幔作为隔离的介质、面具的佩戴与脱落、阴阳符号的对接,男女对峙,真与假,虚与实,均为「影」的语境巩固。虽满满中国元素,但究其创作者的立场、女性角色的设置及外部环境对命运的催化,内核包含黑色片元素,也算其近年创作的折中之法。表演令人刮目,念白也自然,然台词浅白简单,与整体风格不搭;后半段仓促。
本片改编自罗尔德·达尔鲜为人知的短篇故事,主人公是一名专业灭鼠人。